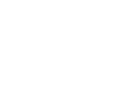搜索网站、位置和人员

电话: +86-(0)571-86886861 公共事务部
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布莱克在长诗《天真的预言》中如此吟咏道,经由我国文人徐志摩翻译后,更增了几分东方禅意之美。
世界那样浩瀚,探索的步履似乎永远无法停歇;但它也如此触手可及,栖身于我们见到的一树一花、一沙一石中。
恰逢湖心讲堂四周年,9月,“承前启后”的2024年秋季公开课邀请了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研究所所长张杰,与历史学家、澳门大学历史系讲席教授王笛,以“见广大于精微”为题展开探讨:
科学家如何在激光的聚焦下,见宇宙于小尺度之中?人文学者又是如何手持“显微镜”,剖析历史长河中普通人作出的贡献?
在这样特别的一期活动中,湖心再次打破学科疆域,在不同的观察视角中驰骋,让科学与人文的枝蔓在这里交融和解。这是对既有的17场讲座、35位“湖心贤达”的致敬,对一万多名观众及数百万网友的感谢,也是对未来更多对话许下的期待。

01 激光聚变,为何将点亮人类的未来?
作为享誉全球的高能量密度物理领域科学家,张杰目前的主要研究工作聚焦在如何在地球上的实验室中实现太阳中的核聚变反应,以期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再造太阳”。他是首位获得世界激光聚变与高能量密度研究领域最高奖——爱德华·泰勒奖章的华人科学家,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交通大学最年轻的校长。他的演讲从一个五岁的男孩给他爷爷奶奶讲可控核聚变的故事开始,轻松幽默、深入浅出,一下子就把台下来自社会各界数百名的观众的注意力吸引到激光聚变反应上。
与我们社会上目前核电站所依赖的从较重的元素裂变为较轻元素的核裂变反应反应不同,核聚变反应,是将宇宙中最轻的元素——氢的两个同位素氘与氚融合在一起,在它们融合反应的过程中会释放出比裂变反应还要大几倍的巨大能量。单位质量的核聚变燃料反应所释放的能量,比单位质量的化石能源所释放的能量高数百万倍;而且由于核聚变原料近乎无限、反应过程中无高放射性废物、运行绝对安全、没有碳排放等优点,使之早在半世纪前,就被认为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终极能源。
那么,激光聚变又是什么呢?原来,这是效仿太阳、实现聚变的路径之一,全称为激光惯性约束聚变。而研究的重中之重,是实现“点火”,也就是激光聚变反应输出的聚变能量已大于输入的激光能量,这是人类通往激光聚变电站的重要里程碑。实现激光聚变点火的关键,是极高的温度及极高的密度,温度与密度的乘积就是压强,这个数值需要达到3500亿个大气压,是在地球上非常难达到的条件。
实现激光聚变点火的道路,曲折而艰难,人类走了整整50年。
2022年12月4日,美国利用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家点火装置实现了激光聚变输出能量大于激光输入能量的目标,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下一步,全世界要做的,就是向激光聚变的电站进发。
张杰,正是我国加速推进激光聚变能源发展力量中的一位重量级的身影。
他进一步介绍说,美国激光聚变虽然取得了点火成功,但是其点火方案中还存在加热驱动效率特别低、可控性差的问题。1997年,张杰根据快点火原理,提出了通过四步分解物理过程,实现压缩与加热过程分离从而提高加热效率和可控性的“双锥对撞点火”方案。但是由于一直没有大型激光装置进行实验,因此,这个方案一直没有机会得到测试。2018年,重新返回科研一线的他,组建了一个由300多位研究组成的大型联合研究团队,人员来自6家中科院单位与10所大学。
 张杰
张杰
在过去的5年时间内,这支团队在高功率激光实验室中待的天数为359天,激光打靶共924发次。“做激光聚变实验的人经验与打了多少大能量激光发次成正比,就像飞行员驾机飞行过多少个小时一样,”张杰讲述了研究背后的故事、并向观众解释,“全世界对中国对激光聚变的投入与努力,印象都是非常深刻的”。今年年初,他们实验结果的论文入选美国物理学联合会出版社的“科学之光”,编辑部高度评价了这篇论文,题目是“双锥对撞为高增益激光聚变带来了希望”。
“未来,我们希望建成具有中国人自己的知识产权的激光聚变电站,而且希望那时候的单位千瓦时的电价可以低于美国的,”张杰展望道,“中国研究者从现在到2045年,要快马加鞭,与中国的工业界结合在一起,希望能实现用激光聚变能点亮未来的梦想,迎接核聚变时代的到来!”
02 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为什么亟待启蒙?
把视线从科学转向人文,在人类的社会中,对精微或者说局部的关照,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第二位主讲人王笛,是微观史研究与写作的代表人物,也是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在这场湖心讲堂中,他把上面这个问题作了提炼与升华,转变为一个发人深省的设问:我们需要历史认识的启蒙吗?
“为什么需要启蒙?这(以下)是我对20世纪以及21世纪在历史认识方面的一些思考。”王笛开场道。
历史,有两层含义。第一,从今天往回看,过去的一切都成为了历史。第二,历史学家或历史研究者根据历史上留下来的文献资料(档案、官方文献、口述资料、考古发现等)来重构的过去。
历史有什么用?在哲学家尼采看来,它可以影响一个人,可以影响一个民族,可以影响一个文化的未来。中国改良思想家梁启超也在1902年出版的《新史学》中提到,历史帮助我们去理解自己,去发扬爱国的精神。
然而,历史研究是非常“主观”的——根据同样的资料,用同样的方法,不同历史学家写出来是不同的历史。我们每个人对历史的认识,随着所生长的世界、周围的环境在不断变化,且由于我们的教育、地域、意识形态、政治观点、家庭出生、文化背景等一系列的因素的不同,每个个体对于历史问题都会有不同的解释。
事实上,我们对历史的理解、解释和评价的观点和态度,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过程和历史意义的看法,个体或群体在特定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下形成的理解,这些都是历史观。它提供了解释历史的框架,影响我们对过去的解释,对当前和未来的看法。
 王笛
王笛
在中国,居于主导地位的是帝王史观与英雄史观,我们学过的历史,几乎都是国家或统治者的历史,关注的是帝王将相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王笛这样的历史学家正在做的,是把大家的视角从帝王史观、英雄史观转向民众史观与日常史观。
帝王史观下的历史写作,几乎完全忽略了老百姓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对于大量百姓的牺牲,他们的鲜血和生命,在历史的记录中被轻描淡写。其实,王朝更迭、日月变幻,谁是社会稳定与繁荣的基础?王笛说,是千千万万个普通人,靠的是一代又一代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平凡的日常事务,就是我们作为普通人对这个社会所能做出的最大贡献,“我们一点也不需要为做一个普通人而感到羞愧”。
也正因如此,在读历史的时候,一定要带有批判的眼光,对帝王和英雄史观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同时,人人都是历史学家,在今天,记录手段变得越来越方便,手机可以拍视频、录语音、写文字,在以后,这些素材可能就会成为历史学家研究这个时代的最珍贵的资料。
“从宏大回归日常,用记录对抗遗忘。”演讲末了,王笛以一句精练的倡议进行了总结。
03 面向未来,我们可以做什么?
在湖心讲堂的场域里,观众,向来是构筑精彩讨论的重要身影。台上,是通过传递与分享知识精华的湖心贤达;台下,是通过问答环节积极参与头脑风暴的社会大众。在这一场的问答环节,观众们向物理学家张杰、历史学家王笛及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提出的问题,立足个人行动,展望未来世界。
问:作为高中生,我很想知道无论是学文还是学理的同学,该以怎样的姿态拥抱历史与未来相互交融的新态势?
王笛: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正面临一个转折,每一个年轻人都面临着不确定性,比如我到底选什么专业,这个专业出来以后能否找到工作,等等。我们现在也经常听到年轻人要躺平了,我知道大家所说的“躺平”是一种无奈,其实也是对社会的一种批评。我们对于未来,无论自己有怎样的定位,都一定不是躺平能达到的,馅饼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要随时做好准备,当我们有了机会,就一定能去争取。我们对自己要有一个追求--也不是说大家都要在一条路上,可以有各种选择,做你们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是很重要的。
张杰:你马上就要开始上大学了。大学对社会影响最大的是大学精神,大学精神由两部分组成: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所以,你不管是学文还是学理,要想了解未来,给未来做贡献,一定要文理兼通。在学理时一定不要“废了"文科,同样,在学文的时候一定不要随便将高等数学、物理学扔掉。
施一公:工业革命以来的200多年里,从科学技术角度看,人类似乎是在指数进步的。我们尽享技术进步带来的优惠与便利,先进科学技术的出现让我们每个人获得了更多的可能,但也让我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产生了不安和焦虑,甚至到了一个临界点。我觉得大可不必,不要忘了,技术都是人创造的,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的价值观,看世界的观点。与其被现代科学技术蜂拥而至带来的喧闹打乱了脚步,不如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作为人应该怎么看今天的世界。而这样一个看世界的观点最根本的还是你的思辨能力,就是批判性思维。只要有独立思考的看世界的能力,你就能够活得明白,不至于轻轻松松地被别人带偏。
问:在您的研究经历中有哪些成功的跨学科合作案例可以分享?您认为哪些学科或技术的融合将对您的研究领域产生最为显著的影响?
施一公:所谓合作,一定是你遇到一个瓶颈,需要其他学科、其他专家来帮助你的时候,才能做得更好。如果我只做生物物理、结构生物学,只去看物质结构、蛋白结构,也许我不太需要这样的合作,但我只要再跨出一步,我就需要物理学界、数学界、医学界的学者来帮助我。我的实验室非常关注人类对于一些自然现象的感知,比如对光、声、电、磁的感知,我们已知的现象是很有限的。为了将这个课题推到下一个水平,我也很幸运地找到一位理论物理学家、一位医生、一位做微纳电子器件的电子学专家加盟我的团队。几乎所有的研究,我个人觉得都需要跨学科的合作、向别人请教合作,才可能做得更精彩,不然不就是闭门造车吗?
王笛:其实多学科的交叉可以说对我的学术发展有着绝对性影响,且这应该归功于我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训练。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历史系非常清楚的一个规定,每个博士生必须要修四个领域,只有两个领域可以在历史系。所以我在历史系修东亚史、美国社会文化史,在人类学系选修的是社会人类学,在政治学系修的是比较政治学。多学科的学术训练,在我后来研究成都的街头文化、茶馆和袍哥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要用相当多的精力进行田野考察,如果没有人类学的训练,就不可能完成这些考察;政治学让我在思考日常生活的时候,去思考政治问题,所以我在街头文化那本书中有一章是研究街头政治的;在茶馆的研究中,去研究茶馆中的政治、公共空间的政治。
张杰:首先我想提醒大家,学科是在人类认识自然世界和社会科学时对知识体系的一个分类方法,所以它是第二性的。而第一性的科学研究问题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的。以物理学为例,物理学家存在的价值在于解决两类挑战。一类是自然世界中最难于理解的挑战。另一类,是人类社会在快速向前发展时,碰到的瓶颈性挑战;这些挑战都不会是专门针对某一门学科出现,解决这些挑战,一定需要综合大量知识、跨很多边界。比如激光聚变的挑战,我现在的300多人的团队中,既有物理学家,也有化学家,也有工程师,同样还有AI科学家、能源科学家、电气工程师。只有这样,这个团队才有可能去解决激光核聚变当中出现的问题。
问:公众如何成为参与科研的力量,构成从科学发现到创新变革的桥梁?
王笛:其实任何事情都需要公众的参与。科学当然是高精尖的,需要专业的人才。历史研究需要专业的历史学家,但其实人人都是历史学家,都可以写下自己的故事,这就是公众的参与。科学研究也是这样,像张杰老师所研究的这些高精尖的激光聚变这些,公众没办法直接地参与,但像这种科研一定要受到公众的支持才有长远的发展力量。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公众和科研一定有紧密的关系。
张杰:其实,每个人何尝不都是科学家。科学家需要什么?科学家其实就是对我们自身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好奇心的持续求索。不管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自己,一定要将自己的好奇心抓住,不放过任何问题,你就有可能成为从科学发现到创新变革的桥梁。
施一公:我经常会收到来自一些民间科学家的信件,他们认为通过自己的努力对科学问题已经产生了非常深刻的看法。科学发展至今,我们的科学家一般都是“在高铁上看世界”——从我们上了大学以后就按照现在科学技术的框架在不同的学科学习,不断吸取知识并在已有框架下拓展知识,一直这样下去。即便是交叉学科的合作,也是基于现有框架。对于没有框架的领域,科班出身的科学家一般是不去探索的,这个现象给了无法运用高超现代仪器手段进行科学分析的老百姓一个机会。你可以以你独具的眼光观察自然界,发现一些现象,也许你会提出另外一些不同的理论、假设,可以用这些理论和假设去和科学家交流。所以,其实公众是可以以独特的方式参与科学研究的,但很可能不是像我们那样运用科学仪器和严谨的现在所谓的基于仪器的推理,这样的话你就犯了田忌赛马的大忌,应该用你独特的观察能力去发现问题,然后提出问题来。
最新资讯
学术研究
大学新闻
人物故事
大学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