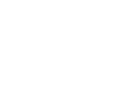搜索网站、位置和人员

电话: +86-(0)571-86886861 公共事务部
行走在人生路上,我们难免会遇到困顿与离别,如何面对是伴随一生的重要课题。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理解命运的波折,是在前行路上给予我们力量和勇气的源泉之一,能够让我们在命运面前满怀希望、坚守初心,以坚韧的信念去面对。
2024年3月21日晚,公益人陈行甲携新作《别离歌》,与中国文化书院院长、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杭州市西湖教育基金会理事长陈越光,为西湖大学的师生带来了一场以公益为出发点的人生感悟对谈。以下为本场对谈的精华内容。
 陈行甲(左)、陈越光(右)
陈行甲(左)、陈越光(右)
我们生而为人,苦难其实是一种常态
陈越光:
此刻,我们在西湖大学,而行甲现在做的工作,本质上和教育有关。怎么来界定教育,什么是教育?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认为,教育有四个功能、一个本质。领悟生命、传承文化、传授知识、规范行为,这是教育的四大功能。但教育的本质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行甲这些年来做的很多工作,都是给生活中那些奔波、落难、困厄之中的人以现实帮助,但渗透在背后的都是灵魂对灵魂的呵护。
我在给《别离歌》写序前是认真通读了《别离歌》全稿的,下面我从《别离歌》开始提问。在《别离歌》里,你讲了那么多故事,你能不能说一说哪一个是最打动你的,或者最刺痛你的?然后再讲一讲,苦难这种灰暗沉重的东西,出现在人们本想阳光明媚的生活中,我们应该怎样正视和看待它?
陈行甲:
大家看书名《别离歌》,如果喜欢古诗词,马上就会想到李煜的那句“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实际上就是从这里拓下来的三个字。我做的公益慈善项目是关于欠发达地区儿童青少年的大病救助和教育关怀,之所以想到用这样一个题目,最开始就是被那些生离死别所打动。
我为什么会想到要写《别离歌》,最初的一个原因是:我和团队伙伴们也经历过很多的压抑,在这些患儿的病房里、家里服务的过程中,在走近他们的过程中,我的心理建设变好了很多。我是慈善基金会和公益项目的创始人,我知道自己不是来点对点、遇谁是谁的那种随机的“救苦救难”,我还是想做社会实验,想探索一下因病致贫这个社会难题的解决办法。
大家如果看我的这本书,会看到第一章中,我的伙伴们在服务过程中出现了心理创伤。过程中的有些“苦”“难”会超过他们的想象。不光经受苦难的人会遭受心理创伤,在旁边陪伴、见证的,甚至试图去拉、去搀扶的人也会。我稍微好一点,稍微站得高了那么一个台阶,我对这些苦难的认识会稍微抽离一点。但尽管如此,我们生而为人,苦难其实是一种常态。
为什么最后我想把它写下来,最开始是基于我需要找到一种方式安放自己的内心。我可以给伙伴们做心理辅导,我也会很关注伙伴们的心理状况。但我自己在很多夜深人静的时候仍然会觉得很难过,这时候有一种方式,就是把它写下来。
我们现在在大病救助这一块已经服务三百多个患儿了,每个患儿都有服务档案和服务笔记,记录着哪一次去探访,哪一次去交流,以及患儿的重要进展,一个患儿就有两万多字。在把它们写下来的过程中,我安放了自己的情绪,安放了自己的内心,也整理清楚了自己的思绪,这对我是有价值的。

当它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我意识到它还有另外一个价值。我们不歌颂苦难,但在苦难中的那些坚守、那些挣扎、那些努力,那种团聚起来拼命的一团火,不能让它灭掉,那样的挣扎和努力特别有力量。
后来我就产生了一种愿望,想为这些人立传。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滚滚向前,生活就像一条波浪宽广的大河,在河面之下、在社会的盲点处还有很多的“小石子”,他们甚至终身都很难被大众看到,但不代表他们没有来过,没有存在过。
为什么我会把阿亮这个孩子写在第一个,是因为我产生了这样的责任感,我想为这样的人立传。阿亮才七岁多,经历过这么重大的疾病和整个家庭的分崩离析,最后离开人世,他来不及看到世间的美好,但也非常努力地活过。我想如果我不写的话,大概率这个孩子就像一粒烟尘消失在这个世间,就像他从来没有来过一样。于是我产生了写的冲动,我要把他写下来。
陈越光:
罗素说,支撑他生命的力量是什么?他的动力是什么?是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这三点支撑着他的一生。倾听苦难是一个人内心力量的表现。我们的老祖宗把有没有这个力量作为界定人和非人的标准,叫“无恻隐之心非人也”。
刚才行甲说,想把这些东西记下来,安顿自己的心。那个七岁的小孩子不可能自己来写,他的家人也不见得有这个能力。当这些东西成为我们完整的历史,便有两个功能:一,当下社会也会重视,来更多地解决问题;二,给历史以持续而完整的记录。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在你来看,进入公益领域之后,最难的是什么?跟以前碰到的不一样的“难”是什么?

陈行甲:
我就想说一个具体的事情。我做儿童癌症综合控制,《别离歌》第二章题目写的是“活着的菩萨”,写了两个孩子,一个是广东省河源市农村的小女孩小莹,一个是青海寺庙里的小男孩,他们都活下来了。
我特别想说的是第一个叫小莹的女孩,让我真正体会到“难”,是跟我过去从政时、跟我自己生活中的艰难完全不一样的体会。面对这种生命的、生活的无常和无奈,有时候你会觉得毫无办法。这个孩子具有极致的典型意义,她的父母是普通农民,一个1981年出生,一个1982年出生,非常辛苦地在城市里打工谋生,有一儿一女。女儿患了急性髓系白血病,非常凶险。化疗、移植,他们整个家庭三代人紧紧团结在一起,同仇敌忾,非常努力。我们慈善组织也给了他们极限的支持,医生团队也非常努力。你能想象吗,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为这个女孩花了两百万,而这个女孩身上出现了“人间奇迹”,她闯过重重难关活下来了。
白血病患者在移植之后可能经受的感染,从盆腔开始到大脑,全部重要器官她都感染了一遍,主治医生和团队说,这真的是医学上的奇迹。在这个过程中她一直没有放弃,她的父母在极端的困难下也不放弃,我们当然也一直没有放弃,陪伴了全过程,那个见证非常煎熬。我想说一个最难的时刻,就是这个孩子经过很多轮治疗后又感染了毛霉菌。
我去医院探访她时,已经不能进病房,我只能在病房外面跟她的妈妈交流。从广州回深圳的车上,我一路流着泪回来,我觉得孩子不是一个人,是她整个家庭、整个医护团队、整个慈善组织,整个社会组织紧紧围绕着她,紧紧地抱着她,但我们仍然无能为力。那个时候,(事情)完全在我们的掌控之外。那一晚她能不能熬过去其实非常有节点性意义,因为医生有很明确的判断,如果过去了,可能又会是另外一种局面。后来这个孩子挺过来了!
您问我在公益路上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我觉得遇到最大的困难是,虽然我有一个社会实验的大框架,从患者、医生、药物,建立数据库,和政府合作各个方面做这么一件事情,但在具体、沉浸式服务一个个患者时,比如碰到这种孩子,会有极度的无力感,面对生命无常时的无奈。我们总安慰人要看开,其实看不开,(看开)很难的。
最后我写《别离歌》的后记时,想到一个非常伟大的医生爱德华·特鲁多,他的墓志铭是“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ve Often, To Comfort Always”,偶尔是治愈、常常是缓解,总是去安慰。
我经历了一个个孩子,特别是如此特殊的孩子,这一关我也过来了。他们来求助我时,我会感觉很高兴。越光老师,您能体会我说的这种感觉,我们共同走过最难的时刻后,已经是一家人,我们已经是一体的。真的是“I'm so happy I can help”(很高兴我能帮助你)。
怎么理解“人生之终”?
陈越光:
今天为什么我要让行甲来讲做公益的难处,因为你们如果去参与、去做都有可能(面临这些情况)。当然,也不是每件事情都是这样做,但总体上、严格地来说,做公益一定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微量资源、有限责任、无限情怀,在这中间要做好平衡。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从《别离歌》出发,讨论怎么来看苦难;接着,我们看怎么做公益,看投身公益背后的难处。这两者的联系是,如果不能真正理解人生的苦难,就没有动力支撑你以微弱的资源、有限的责任去面对无限的情怀,这是一致的。
我们再往前走一步看。行甲年过五十岁了?
陈行甲:
我是1971年出生的,今年五十三岁了。
陈越光:
你都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了,可以来掂量一下命运了。今天对谈的主题是“以终为始在人生路上”。“以终为始”用在人生上还是有创意的,物有本末、事有终始,这是《大学》的话。比《大学》更早的《黄帝内经》,有一篇“终始篇”,这里的“终”与“始”,都是讲具体的事与物。
我想问你的问题是,你怎么理解“人生之终”?其次,你怎么看待不同年龄段中人和事业之间的相处,以及人对命运的理解?

陈行甲:
谢谢越光老师的问题,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考题。
以终为始,我怎么理解“终”?我做的是儿童癌症综合控制(项目),做大病救助,服务过三百多个孩子,其中83%是活着回来的。虽然孩子的救治成功率这么高,但这是一个重症,注定有将近20%的孩子会离开人世。我顺便向越光老师汇报工作进展,我在和公益伙伴李治中(菠萝医生)一起来做这么一件事情。
中国每年的癌症发病率是十万分之二百九十三,每年有大约四百二十万人患癌症,其中1%,也就是大约四万个孩子要患癌症。按照现在平均的治疗成功率计算,每年至少有一万个孩子要离开人世。但是在现阶段,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几乎没有一张儿童临终关怀的安宁疗护病床。所以走到终末期的癌症患儿就很难。
我们尝试做一件事情,在三个城市,马上扩展到四至五个城市,建设高水平的、对标西方发达国家的儿童临终关怀安宁疗护病房。我们希望将来形成一个网络,在整个中国,以二百公里为半径,每一个走到这个阶段的家庭和孩子,都能找到一张安放他、接收他的病床,陪他有尊严、温暖、平和地走过最后这段时间。
“终”,我见证过这个“终”是什么样子的。近二十年里,我自己有三位至亲离开人世。对这个“终”,我是有很深的感受。这本书最后定名为《别离歌》的意义,就在于人生就是一场别离。说得简单一点,每个人一出生就被判了“死刑”,每个人都是要死的。因为人最终都要离开,所以人生旅途的过程才有意义,它有温暖,有温情,这才是我们活在人世间的意义。
在我经历过自己家庭这些变故,又做这样的事情之后,我对“终”有了很深刻的理解。我不知道我的(生命终点)哪一天来临,但越光老师,我能在内心里比较清晰地看到它。
越光老师,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您曾对我说:“希望你穿越人生的成长,到最后的状态是,像一根小草在土地上面,贪婪地、平和地吸收着阳光和雨水。你最后完成的事情,像最初一样完整清晰。”
越光老师,您当时跟我说的这句话,我都做了记录。穿越人生成长,到最后“以终为始”的话,我觉得“终”就是那个样子。因为我看到了这个“终”,回过头来,这一段(人生)不管它有多少年,我要让它活得有价值。
越光老师最开始和同学们分享的这一段话,我愿意和同学们再分享一下原文,作为学生对老师的呼应,“what I have lived for”,罗素说:“Three passions, simple but overwhelmingly strong, have governed my life: the longing for love, the search for knowledge, and unbearable pity for the suffering of mankind。”
“我为什么活着,三种强烈而又强烈的情感在支配着我的人生: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渴求,以及对于弱势者困难难以遏制的同情心。”
现在我已经来到人生的下半场。在这个路途中,这三种力量在支撑我。对爱,我仍然有渴望,对知识仍然有渴求,对弱势者的困难有痛彻肺腑的怜悯,有难以遏制的同情心。
我也是从二十几岁、三十几岁一步步过来的。我愿意和同学们分享的是,在你们人生最初的阶段,记住越光老师今天分享的罗素文章中的三个要点。不一定要全部理解,但先记住它,让它在你的记忆中,在你的知识体系中,在你的感受中,哪怕你把它当成一篇英文美文来背,让它慢慢渗透在你的意识中,会起作用的。
我最后想说的是,一代人终将老去,可总有人正年轻。

陈越光:
谢谢行甲,行甲总是充满着激情,也有很多思考和很强的行动能力。
我们真正看终点时,没有终点。我在《别离歌》的序里说“生离死别后的生死相依”,我想你们中也有人面对过爷爷奶奶这辈人的去世,你对他们的感情不会这样戛然而止,这种生离死别之后的生死相依,就是历史的本质:可以在今天的人心中复活的过去。
今天所有能为我们理解的人类的思想、观念都是在“轴心时代”开始的。“轴心时代”以前都是文明的碎片,它存在过,但未被理解。为什么“轴心时代”被称为历史的开始?因为人类开始反思自己和自己的历史,他提问了,最深刻的问题就是面对生命的短暂和万物的永恒,人何以永恒?
因此,在这个追求永恒的过程中,回到行甲刚才说的,我们最终如何追求?也许你们在孤独、困惑、夜深人静时会问,“我现在读博士就想把论文写出来,然后,最好留校在大学里搞研究、当教授”,再然后呢?你不断地问下去,人生到底是有意义还是没意义的?
我在你们这个年龄时,不断问这个问题,问到头了一定是走向轰轰烈烈。今天我来想什么是人生的意义,人生有没有意义?有意义,意义就是一种牵挂,你还有各种各样的牵挂,对亲人,对他人,对世界。
生命是珍贵的,为自己的生存做的努力也是可以感天动地的。一个穷苦中的人为了改变命运所做的努力,为了吃饱饭所做的努力,具有天然的正当性。但当这种努力不仅仅是为个人,而且是为弱小者,它的正当性能加万倍。如果努力是普济他人、普济众生的,那么这种意义会再加万倍。所以意义就是牵挂的扩展和传递。
谢谢行甲带给我们的这个晚上,有思考,也有行动,但我想更多的是对人生、对事业带着感情的追问。
最新资讯
学术研究
大学新闻
人物故事
大学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