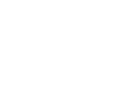饥饿回忆,如果肠知道
有趣的实验
2023年11月28日
媒体联系
张弛邮箱: zhangchi@westlake.edu.cn
电话: +86-(0)571-86886861 公共事务部
当11513份肠道菌群数据在面前跳跃,苟望龙总会想起爷爷爱吃的杂粮散饭。 当时的苟家岔白日耀眼,老人们喜欢在村口晒太阳回忆往事。世界新生伊始,苟望龙的记忆大概开始于此,他常听老人们说起挨饿的日子。 苟望龙出生于1991年,去年从西湖大学博士毕业,成为郑钜圣实验室的一名博士后。 他记忆中的苟家岔在哪呢?在鸡川镇。鸡川在哪呢?在通渭县。通渭在哪呢?在定西市。定西在哪呢?在甘肃,在中国的西北。 定西有三大宝——洋芋、土豆、马铃薯。因为定西缺水啊,穿城而过的河流有三条:东河、西河、官川河。都是季节河,浑浊的河水只有在夏日暴雨后才会涌上。但流传在当地的民歌里,处处充沛着江和海:江是江来海是海,
江海岸上一只船。
船帮水来水帮船,
珍珠玛瑙镶船边。
真的很奇怪,一个缺水的地方,为什么民歌里都是大江大海大船?小望龙也不太理解,爷爷为什么那么爱吃散饭。把杂粮磨成粉,再煮成糊糊,配点咸菜,能成就爷爷最满足的表情。爷爷经常把小望龙叫过来:“碎娃娃,来,尝一口。” 这娃娃尝了一口就不愿意第二口了。这份最初的味觉记忆来得平淡无奇,只是爷爷总当着他面吃得很香。对于土豆的爱,倒是一直伴随着苟望龙,直到他来到杭州读博士,可以在食堂同时点上两种口味的土豆。
苟家岔的卫星地图
杭州是真真正正处处有水,苟望龙已经在这里生活了近5年。早在硕士阶段,他主攻计算生物学,开发计算算法解析生命数据。博士阶段呢,他要探索的对象有点特殊。它们虽在我们身体的躯壳里,却是另一种生命;它们微不足道,又浩浩荡荡。 有研究认为,人体肠道内寄生着约数万亿个细菌,在漫长的生命演化历程中,它们和人类形成了共生的关系。它们帮助人体消化食物,合成必需的短链脂肪酸,还能帮助清除毒素,支持肠道功能。 但别以为菌群只是和肠道搭伙过日子,吃点残羹剩饭。西方有谚语We are what we eat,翻译为人如其食,或者说,恰如其“粪”。你的食物,也是肠道菌群的食物,血液中有部分的小分子物质,是肠道菌群代谢产生或者修饰的,这些生物化学信号会反过来作用于你的身体,包括大脑。 而肠道菌群呢,本身是一个可以相互感知相互影响的复杂网络。就像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小说《绿孩子》呈现的场景,绿色精灵们抱在一起睡在树洞里,身体会长满青苔,人类便不能发现它们。而它们所有的梦都是相通的,每个人做的梦,都会出现在另外一个人的梦里。 肠道中的这些精灵,是苟望龙博士阶段的研究对象。导师郑钜圣当时刚回国不久,加入西湖大学,准备开拓在肠道菌群领域的研究。在这里,学生和导师的办公室都在一起,有什么问题要交流,吼一声就能听到。
图源:HEHO
几年很快过去,实验室从云栖校区搬到云谷校区,经历了疫情三年,听着杭州的雨下了又停,停了又下,苟望龙的博士阶段将告尾声。在日常浏览文献的时候,他的注意力被一个单词拖住了——Famine——饥荒。 打记事起,他就在村里听老人们讲饥荒的故事。他给我讲了其中一个。一个孩子已经死去,当负责赈灾的统计员来到家里,家人给孩子侧身盖上被褥,露出小脚丫,孩子仿佛正在熟睡。这样可以多分到一份救济粮。 苟望龙看了更多文献,都指向一个结果——生命早期经历过饥荒,成年后发生糖尿病等代谢类疾病的几率会增加。最早,这些研究发源于一个理论猜想。20世纪90年代,英国的David Barker教授提出了多哈(DOHaD)学说,认为除了遗传和环境因素,许多疾病可能是由于在子宫内或儿童时期的不良暴露——如营养不良、致癌物等——所造成的。 David Barker凭什么这么说?他真实调查了24114位女性,她们曾是1944年到1945年荷兰饥荒时的孕妇,发现她们的孩子长大后,心血管疾病、糖代谢异常、肥胖等一系列代谢性疾病高发。 荷兰饥荒又被称为“饥饿的冬天”(The Hunger Winter),彼时二战已经接近尾声,但荷兰还处在德军控制中。之前荷兰铁路罢工,使德军物资运输受阻,为了报复,德军切断了荷兰的食物运输。饥荒发生时,纳粹德军却也绷不住了,反向盟军求援。于是,有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名场面:盟军的三架战略轰炸机卸掉炸弹,装满食物,飞越德军火力区,分两批共计11000吨向荷兰空投。 在饥饿的人间,漫天的罐装食品、干货、奶酪和巧克力从天而降。德军也信守了承诺,没有开火。饥饿的冬天过去了,战争结束了,科学家意外获得了难得的研究样本,除了启发了多哈理论,有科学家发现饥荒可以影响遗传物质,通过改变组蛋白修饰影响基因表达。 这样的事件,被称为自然实验,因为不是实验室可以完成的,尽管它看上去一点也不自然。
正在装载食物的盟军飞机。图源 Imperial War Museums
“饥荒会不会改变肠道菌群?”苟望龙非常自然地提出了自己的问题。 回想苟望龙开始读博士是在2018年,那年西湖大学正式建校。几年的博士生涯,他参与的第一个课题就是肠道菌群和2型糖尿病的关系。郑钜圣在美国和英国的时候,一直从事营养学和流行病学的研究,糖尿病一直在他的研究视野之中。但要说哪些种类的肠道菌群能够精准预测2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当时仍然没有定论。 尽管有统计数据支撑,但想要证明菌群和疾病的因果关系却不容易,需要更多跨学科交叉的方法,差不多得用上十八般武艺吧,包括传统统计分析、人工智能、小鼠实验、生化分析等等。 基于人群数据,他们先构建了一个具备297个预测变量的可解释机器学习模型,包括肠道微生物构成和其他环境因素。之前的机器学习模型是“黑盒”,人类无法理解中间过程,引入可解释的机制后,研究团队就知道哪些变量起了主导作用。 最终,他们发现21个可以预测2型糖尿病风险的变量,其中13个是肠道微生物菌种,除了有2种被报道过外,其余11种都是他们首次发现。他们基于上述核心菌谱构建了一套2型糖尿病风险评分机制(MRS)。 MRS在不同的肠道菌群样本中预测2型糖尿病风险都有良好的表现,这大大增加了他们的信心。其中一个重要变量就是肠道菌群的多样性,这为后来的研究留了一个伏笔。 为了进一步验证因果性关系,排除糖尿病本身引发的MRS增高,他们对空腹血糖正常的志愿者群体进行了长达三年的随访研究。在249名健康个体中,他们发现, 三年前的MRS值与三年后的空腹血糖增量显著正相关。 此后,他们又分析了血清代谢物与MRS的关系,从分子生物学层面寻找证据,并通过小鼠的粪菌移植实验,发现移植了高MRS宿主肠道菌群的老鼠, 其空腹血糖水平显著高于低MRS组与无菌对照组。这些结果都进一步验证了核心菌谱与宿主糖代谢具有潜在的因果关系。
肠道菌群之间相关性分析。图源:郑钜圣实验室
苟望龙整理了一下发散的思绪。他马上给正在青岛出差的郑钜圣打了电话,简单说了下自己的猜想。郑钜圣当即决定尝试,因为没有人从肠道菌群角度来解释过它。 科学现象就在那里,谁都可以看到,不同的是你有没有对此产生好奇。 苟望龙先进行了预实验,他选择了来自三个不同地域人群的样本——广州市、广东省(和第一个样本不重合)、以及全国(除广东省之外的15个省份的样本),样本量分别是1920人,6560人,3033人。汇总在一起,是11513人的肠道菌群数据,其中有595人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出生的。 苟望龙把那三年出生的,按照出生年份设置为独立的组别,62年以及之后出生的,设定为对照组,而1959年之前出生的,就是在生命其他阶段经历三年困难时期的,比如幼年时期、学龄前时期、学龄时期,成人时期等。 这个简单的尝试,结果让他们大为震惊。三年困难时期的组别,特别是1959年出生的那组,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肠道菌群多样性的下降。一般来说,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菌群多样性也会衰减——三年困难时期出生的人,在采样时60岁左右,但他们的菌群多样性数值比80到90岁的人还要低很多。 再说,之前的肠道菌群研究有一个难点,就是很难在不同地域外推,因为不同地域人群饮食及生活方式等不同,肠道菌群构成差异很大。但这次的结果却出奇一致。这些数据,在图表上形成了三个低沉的山谷。 苟望龙和郑钜圣觉得心里有谱了:“这事儿值得一做。” 三个人群的E1组(1959年出生)都出现了明显的多样性“低谷” 。图源:郑钜圣实验室
三个人群的E1组(1959年出生)都出现了明显的多样性“低谷” 。图源:郑钜圣实验室
数据来之不易,背后都是合作团队的心血,需要工作人员上门进行粪便取样,并观测记录受访者的饮食习惯。随后,通过测序技术,科学家就能为几百种肠道菌种“描摹”出大致分布样貌。统计分析需要小心翼翼,研究团队需要对数据进行矫正,包括测序深度(检测技术本身带来的误差)、饮食和生活方式、疾病、年龄因素等等。 志愿者的平均年龄大致在50到60岁。采样时,他们也许不知道,漫漫人生,记在了心里,也写在了肠里。 结果清晰浮现,生命早期经历过严重饥饿的群体,肠道菌群多样性显著降低,而肠道菌群多样性的降低伴随着2型糖尿病风险的增加。 如同干旱摧残过的土地,再也无法恢复到原来生机勃勃的状态。肠道菌群是固执的,在肠道菌群移植治疗中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即便患者移植了新的菌群,数个月后,依然容易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1961年,广州市民在寻找食物。图源:人民网
每一个人的肠道菌群,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其测序数据多达数百个维度。凭人类的脑子,是无法同时理解数百个数据维度的。他们用到了数据降维的方法,这在菌群研究中是常用的。通过计算,把数百个维度降低到两个主要的特征维度,以此来指代不同的样本结构。这就好比,当我们无法直接描绘一个三维物体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二维的影子来描述它。 结果给了他们第二次震惊。最严重暴露的 E1组,坐标位置显得和其他组别格格不入,他们大多孤立地存在,形单影只,仿佛走失的孩子。也就是说,持续的饥饿不但改变了肠道菌群的多样性,也重塑了它们的结构。 研究团队还进行了菌群网络分析,筛选出这些样本中的核心肠道菌群,同样发现对2型糖尿病起保护作用的核心菌群的丰度减少。这些研究还发现,经历严重饥饿的时间越早,当然这也意味着越持续,对肠道菌群的影响也越明显。 多哈理论关注的是生命早期不利的环境暴露对生命长期的影响,这次的研究,给多哈理论提供了全新的理解维度——生命最初也许不会留下记忆,但在你的肠道留下的印记可能增加未来罹患代谢疾病的风险。 但证明过去对当下又有何意义?结合课题组之前的工作,这些研究将帮助人类更好地理解肠道微生物和2型糖尿病的关系,帮助我们提前判断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并且我们有可能通过改善肠道群菌来干预疾病。 苟望龙上高中后,爷爷经常会想起那段艰难的岁月,也问他:“碎娃子,你读过书,给我讲讲历史。”他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回答,爷爷本就在历史之中啊。2016年,爷爷在晒太阳时突发脑溢血,周围的老人手足无措,抢救了20多天还是走了,医生说是高血压引发的。苟望龙说,爷爷平时吃得很清淡,不应该啊。 而当苟望龙面对11513份肠道菌群数据时,他决定回答。这些数据不再是冰冷的数字,它们跳跃而连接,此起彼伏。他试图伸手去抓住那些微弱而无边无际的旋律:






 三个人群的E1组(1959年出生)都出现了明显的多样性“低谷” 。图源:郑钜圣实验室
三个人群的E1组(1959年出生)都出现了明显的多样性“低谷” 。图源:郑钜圣实验室